摘要:佛教中國化是一個古老而全新的課題,討論此話題,關(guān)鍵要在方法論上有新的突破,此文試圖以中西佛三大詮釋學(xué)為視角,以漢藏佛教為對象,從理論、歷史、現(xiàn)實(shí)三個維度考察佛教中國化的史實(shí),提出共殊本體詮釋學(xué)的概念。
關(guān)鍵詞:詮釋學(xué) 佛教 佛教中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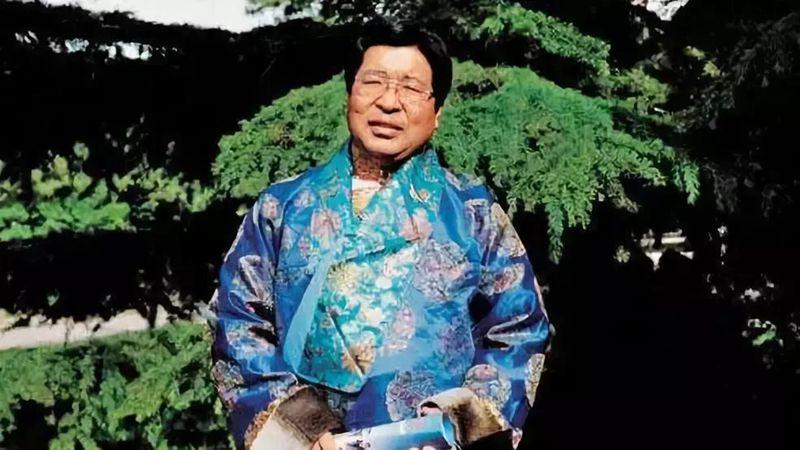
佛教中國化從古人所謂“華化佛教”到習(xí)近平總書記近來提出“堅(jiān)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這是一個古老而全新的課題,討論此話題,在方法論上有新的突破是至關(guān)重要的。為此,筆者接觸到了詮釋學(xué),學(xué)習(xí)了近年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出版的系列詮釋學(xué)的論著及譯著,收獲很大。
現(xiàn)在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在佛教中國化的史實(shí)個案與詮釋學(xué)之間找到一種最佳的契合點(diǎn),從而在前史后論,史論結(jié)合的維度獲得佛教中國化的自然而然必然性,合情合理合法化的結(jié)論。為此筆者試從理論、歷史、現(xiàn)實(shí)三個維度論述佛教中國化與詮釋學(xué)的關(guān)系。
一、理論維度
筆者試從西方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國傳統(tǒng)詮釋學(xué)、佛教詮釋學(xué)三個方面討論佛教的中國化問題。
1、西方哲學(xué)詮釋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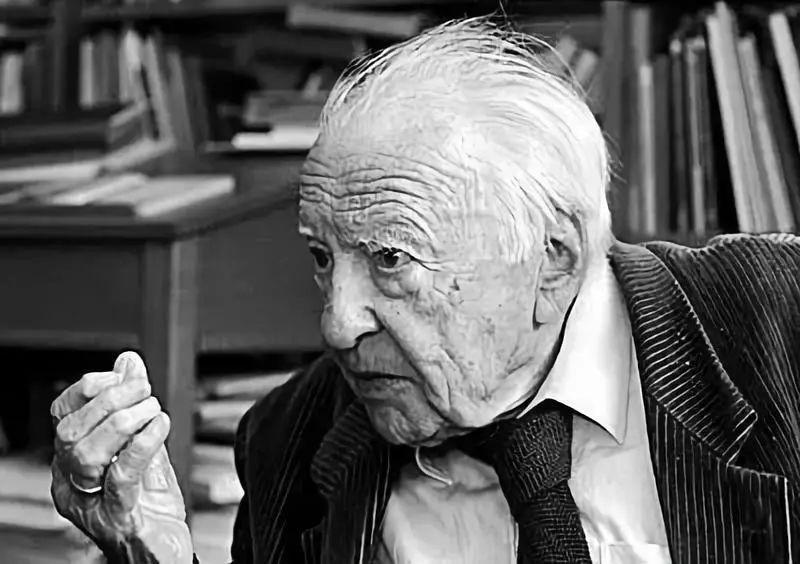
德國哲學(xué)家伽達(dá)默爾
歷史從哪里開始,邏輯也應(yīng)該從哪里開始,用詮釋學(xué)來梳理、分析佛教的中國化,找準(zhǔn)詮釋學(xué)的邏輯起點(diǎn)十分重要,我認(rèn)為它的邏輯起點(diǎn)在:西方詮釋學(xué)經(jīng)歷了從方法論詮釋學(xué)到哲學(xué)詮釋學(xué)的轉(zhuǎn)換過程,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哲學(xué)思潮,這便是海德格爾與伽達(dá)默爾的哲學(xué)詮釋學(xué),它要解決人們的理解何以可能,如何實(shí)現(xiàn)的問題。其用以下詮釋學(xué)話語解答: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存在是我們理解的存在;存在是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這也許是一個主觀唯心論的命題。
我理解哲學(xué)詮釋學(xué)也承認(rèn)客體第一性,主體第二性,存在第一性,思維第二性,但是他所謂的客體,只是相對于主體的哪個客體,相對于思維的哪個存在,也就是作為文本的哪個客體和存在。在這一點(diǎn)上,佛教也和哲學(xué)詮釋學(xué)有相同的進(jìn)路,它將客體外境定義為:可知曉、可明了,所知與外境異名同謂,所知與能知是統(tǒng)一的。此哲學(xué)問題轉(zhuǎn)換到詮釋學(xué)話語系統(tǒng)中便形成了:
首先,文本原義、作者原意與不同時空境遇中的讀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拉鋸式的內(nèi)在張力,用辯證法講即是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一方面讀者要探尋文本的原初意義與作者的原生性意義。另一方面,任何讀者的理解與解釋都依賴了讀者的前理解、前見解,前把握,它為讀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這是促成創(chuàng)造性理解與本土化詮釋的前提條件。
對此內(nèi)容,潘德榮先生的解讀是:“文本的意義不是先于理解而存在于文本之中,它事實(shí)上是讀者在自己的視界中所領(lǐng)悟到的意義,或者確切地說,是理解主體自身的視界與特定的歷史視界的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意義。文本(一切歷史流傳物)在它所依賴已產(chǎn)生的歷史視界中的含義與在理解主體的視界(我們的當(dāng)今視界)中蘊(yùn)含的意義是不同的,在理解中,這兩個視界融而為一,成為一個更為廣闊的視界。它乃是包容了歷史和現(xiàn)代的整體視界。理解,從根本上說,就是‘視界融合’。在這個視界中,文本呈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被理解到的意義。它是歷史的產(chǎn)物,攜帶著它固有的歷史性進(jìn)入了讀者的當(dāng)今視界,并在讀者的視界中獲得了現(xiàn)實(shí)的意義。”文本原義、作者原意與詮釋者理解之間的關(guān)系是怎樣的,如何處理?這便是佛教本土化,中國化與詮釋學(xué)之間的契合點(diǎn)。
西方有貝蒂與伽達(dá)默爾的不同定向,貝蒂提出了四種詮釋規(guī)則:詮釋的客觀之自主性原則;整體原則;理解的現(xiàn)實(shí)性原則;詮釋意義之和諧原則。伽達(dá)默爾說,沒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詮釋學(xué)的立場就是讀者的立場。伽達(dá)默爾在談到詮釋學(xué)的任務(wù)時指出:“對于這個問題的兩種可能回答的極端情形在施萊爾馬赫和黑格爾那里表現(xiàn)了出來。我們可以用重構(gòu)和綜合兩個概念來描述這兩種回答。無論對施萊爾馬赫還是對黑格爾來說,一開始就存在著面對傳承物的某種失落和疏異化的意識,這種意識引起他們的詮釋學(xué)思考,然而,他們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規(guī)定了詮釋學(xué)的任務(wù)。”“施萊爾馬赫——他的詮釋學(xué)理論我們以后還要加以討論——完全關(guān)注于在理解中重建一部作品的原來規(guī)定。”由此看到,在伽達(dá)默爾看來,施萊爾馬赫主張,理解是對作者原意和文本原義精確的重構(gòu)與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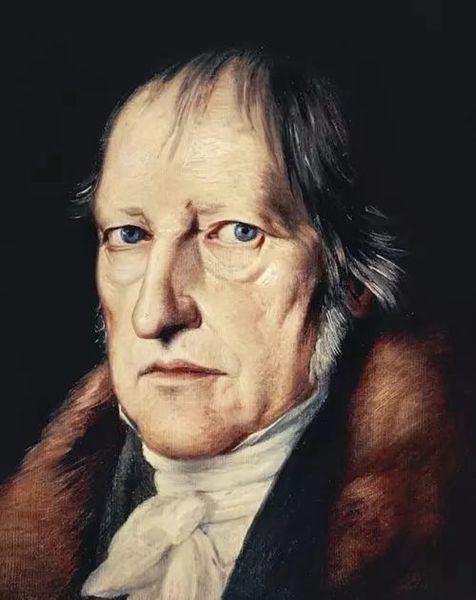
德國哲學(xué)家黑格爾
對此,伽達(dá)默爾則說:“鑒于我們存在的歷史性,對原來?xiàng)l件的重建乃是一項(xiàng)無效的工作,被重建的、從疏異化喚回的生命,并不是原來的生命。這種生命在疏異化的延續(xù)中只不過贏得了派生的教化存在。”從此可知,伽達(dá)默爾對施萊爾馬赫的觀點(diǎn)持否定態(tài)度,他贊同黑格爾的觀點(diǎn):“黑格爾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使詮釋學(xué)工作的得和失相互補(bǔ)充。黑格爾極其清楚地意識到所有修復(fù)的無效性”,在黑格爾看來,理解和詮釋的有效途徑是歷史和現(xiàn)在、客體和主體、自我和他者之整體綜合。這就正如伽達(dá)默爾所講的:“這里黑格爾說出了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真理,因?yàn)闅v史精神的本質(zhì)并不在于對過去事物的恢復(fù),而是在于與現(xiàn)時生命的思維性溝通。······這樣,黑格爾就在根本上超過了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xué)觀念。”據(jù)此說明,在理解和詮釋問題上主張“綜合創(chuàng)新”的黑格爾超越了強(qiáng)調(diào)“還原和重建”的施萊爾馬赫。
其次,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依賴于理解者和解釋者的前理解。伽達(dá)默爾說:“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rèn)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rèn)為是一種置身于傳統(tǒng)過程中的行動,在這過程中,過去和現(xiàn)在經(jīng)常地得以中介”。因此“一切詮釋學(xué)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正是這種前理解規(guī)定了什么可以作為統(tǒng)一的意義被實(shí)現(xiàn),并從而規(guī)定了對完全性的先把握的應(yīng)用”。前理解或前見是歷史賦予理解者或解釋者的生產(chǎn)性的積極因素,它為理解者或解釋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這就是伽達(dá)默爾所謂的“視域融合”,在視域融合中,歷史和現(xiàn)在、客體和主體、自我和他者構(gòu)成了一個無限的統(tǒng)一整體。
這樣,我們就達(dá)到伽達(dá)默爾所謂“效果歷史”這一詮釋學(xué)核心概念了。他解釋道:“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tǒng)一體,或一種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shí)在以及歷史解釋的實(shí)在。一種名副其實(shí)的詮釋學(xué)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shí)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這樣一種東西稱之為‘效果歷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按照伽達(dá)默爾的看法,任何事物一旦存在,必存在于一種特定的效果歷史中,因此,對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須具有效果歷史意識。
他寫道:“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于某個被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如此看來,詮釋學(xué)任務(wù)不是單純的復(fù)制過去,復(fù)制原作者的思想,而是把現(xiàn)在與過去結(jié)合起來,把原作者思想與解釋者的思想溝通起來,形成兩者的視域融合。理解乃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真實(shí)的歷史的實(shí)在與對歷史理解的真實(shí)在,本來的歷史與寫的歷史的關(guān)系,要處理好。這便是詮釋學(xué)的應(yīng)用功能或者說是實(shí)踐維度,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我們要對任何文本有正確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和某個具體的境況里對它進(jìn)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時候都包含一種旨在過去和現(xiàn)在進(jìn)行溝通的具體應(yīng)用。
再次,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我們只有通過語言來理解存在,或者說,世界只有進(jìn)入語言,才能表現(xiàn)為我們的世界。語言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語言與世界的關(guān)系不僅僅是單純的符號與其所指稱的事物的關(guān)系,而是摹本與言行的關(guān)系,正如摹本具有使原形得以表現(xiàn)與繼續(xù)存在的功能,語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現(xiàn)和繼續(xù)存在的作用,因此伽達(dá)默爾說,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就此而言語言觀就是世界觀。佛教文本經(jīng)、論、律的翻譯與佛教的本土化、中國化問題緊密聯(lián)系。
伽達(dá)默爾說:“(詮釋)的任務(wù)卻恰好在于把一種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方式表達(dá)的東西翻譯成可理解的語言”。西方詮釋學(xué)“最基本的含義就是通過翻譯和解釋,把一種意義關(guān)系從一個陌生的世界轉(zhuǎn)換到我們自己熟悉的世界。”據(jù)此可知,伽達(dá)默爾本體詮釋學(xué)所理解和詮釋的對象是本土學(xué)者對傳入其地的外來思想文化的理解和詮釋。因此,本土學(xué)者承擔(dān)著著通過理解、翻譯和詮釋將一個陌生的意義系統(tǒng)植入到自己熟悉的本土思想文化中的任務(wù)。用中國特有的“格義”概念說,以本土固有的大家熟知的經(jīng)典中的概念來解釋大家尚未熟悉的理論概念和義理系統(tǒng)。
伽達(dá)默爾說:“一切翻譯就已經(jīng)是解釋,我們甚至可以說,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語詞所進(jìn)行的解釋過程。”“我們?nèi)匀灰詫δ吧Z言進(jìn)行翻譯為例,在對某一文本進(jìn)行翻譯的時候,不管翻譯者如何力圖進(jìn)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設(shè)身處地把自己想象為原作者,翻譯都不可能純粹是作者原始心理過程的重新喚起,而是對文本的再創(chuàng)造,而這種再創(chuàng)造乃受到對文本內(nèi)容的理解所指導(dǎo),這一點(diǎn)是完全清楚的。同樣不可懷疑的是,翻譯所涉及的是解釋,而不只是重現(xiàn)。”
從歷史到現(xiàn)在,中國的高僧大德將印度佛教的文本經(jīng)、論、律整體的翻譯為漢語文和藏語文,讓印度佛教講了中國話。這不僅是世界翻譯史上的偉大奇跡,也是外來佛教最深刻的本土化、中國化。
2、佛教詮釋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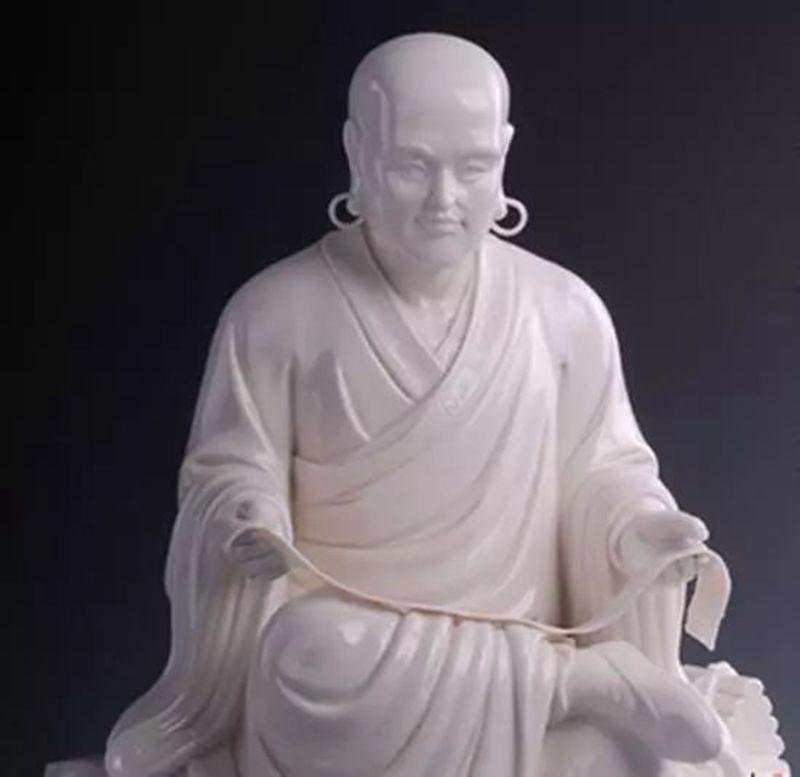
東晉高僧僧肇大師
我們討論了西方哲學(xué)詮釋學(xué)后再看佛教的詮釋學(xué),佛教的要義即“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有些高僧將其總結(jié)為,“覺悟人生,奉獻(xiàn)人生”。 這就是說,佛教的根本宗旨是要人們理解、詮釋、覺悟宇宙及人生究竟實(shí)相。它要解決理解何以可能?理解如何實(shí)現(xiàn)問題?佛經(jīng)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這是佛教的覺解本體論,它所呈現(xiàn)出來的便是經(jīng)典文本的原創(chuàng)性、普遍性、真理性與理解者的個體性、前見性、現(xiàn)實(shí)性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運(yùn)動,它的理論基礎(chǔ)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義。對此,漢地佛教法藏的解讀是“萬象紛然,參而不雜。一切既一,皆同無性;一即一切,因果歷然”。“一多相容不同門”。
藏傳佛教中,第四世班禪羅桑確吉堅(jiān)贊的闡釋是:“俱生和合大印盒、五俱一味四種字、能息能斷大圓滿、中觀正見引導(dǎo)等。各個安立多名言,通達(dá)了義教言者,及有證驗(yàn)瑜伽士,考察之后即明見,究竟旨趣落一處。”這是說,佛教的根本義理是一,其表達(dá)方式是多。據(jù)此說明詮釋學(xué)不僅是哲學(xué)和哲學(xué)史的進(jìn)路,也是佛教的根本進(jìn)路。馮友蘭先生在講到僧肇的佛學(xué)思想時說:“第一個課題是講諸法實(shí)相,第二個課題是講怎樣正確認(rèn)識諸法實(shí)相,第三個課題是講正確認(rèn)識諸法實(shí)相人的精神境界。佛教的各派都要解答這三個課題,不過各派的說法各有不同。古今中外一切大哲學(xué)家所要解答的也就是這三個課題,不過各家的說法各有不同。”馮先生的這一概括用詮釋學(xué)的語言講,作為對象的文本,對此文本的理解與詮釋,由此而達(dá)到的視域融合或曰精神境界。
3、中國傳統(tǒng)詮釋學(xu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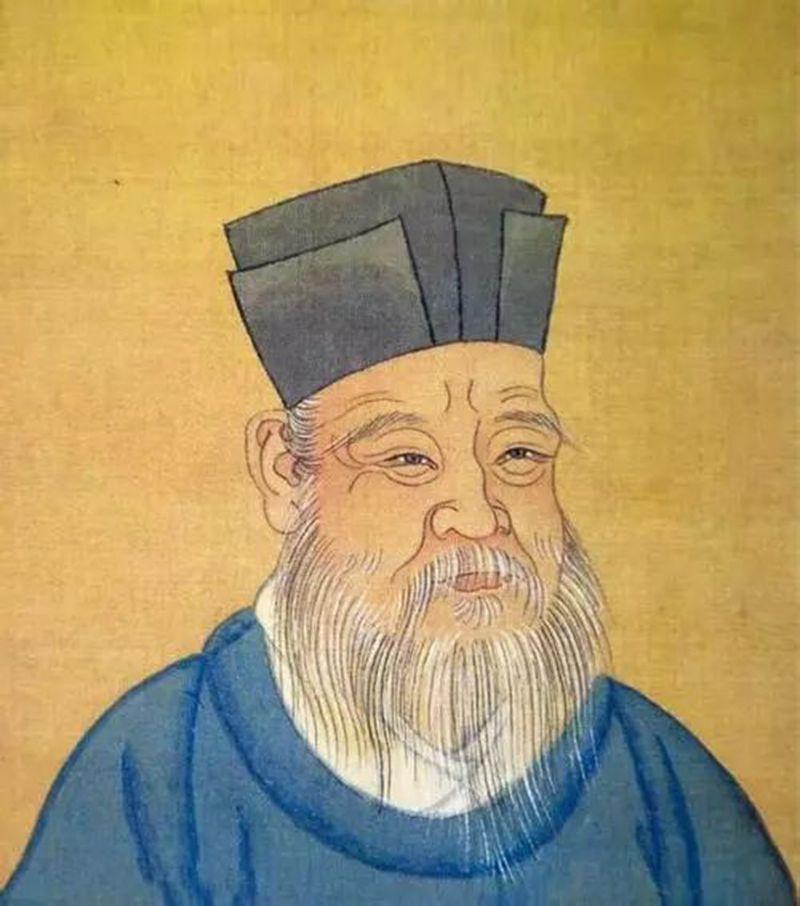
南宋理學(xué)家朱熹
中國是文明古國,詮釋思想很發(fā)達(dá),但中國的詮釋學(xué)只具有方法和工具的性質(zhì),還具備作為“學(xué)”的哲學(xué)蘊(yùn)涵?學(xué)術(shù)界有不同的看法。湯一介先生指出:“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的解釋理論與方法來討論中國的‘解釋學(xué)問題’”。余敦康先生說:“詮釋學(xué)是哲學(xué)和哲學(xué)史的唯一進(jìn)路。中國哲學(xué)的根本方法是詮釋學(xué)的方法。”
據(jù)筆者不成熟的看法,中國傳統(tǒng)詮釋學(xué)集中體現(xiàn)在宋明理學(xué)中,例如朱子:理一分殊,月印萬川。朱熹說:“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朱子語類卷一)“萬個是一個,一個是萬個”(朱子語類卷九四),認(rèn)為千差萬別的事物,歸根到底不過是統(tǒng)一的理的分殊而已。萬物歸結(jié)為一個理,一個理體現(xiàn)為萬物。又說:“萬物皆有理禮,理皆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朱子語類卷十八)就是說作為最高本體的理,由于所居住地位不同而體現(xiàn)出來的作用也不同。
再是,把理事的本末,體用的含義,延伸為一般和個別的意義。朱熹在回答“萬物各具一理,萬里同出一源”的問題時說:“一個一般道理,只是一個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窟便有大窩窟水,小窩窟便有小窩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個別,只是一般水。”(朱子語類卷十八)這里講的“一般道理”、“一般水” 實(shí)際上就是抽象的絕對概念,朱熹認(rèn)為具體事物體現(xiàn)了“一般道理”,大坑水、小坑水、樹上水、草上水體現(xiàn)了“一般水”。
十分明顯,“一般道理”和具體事物,“一般水” 和大小坑里以及木草上面的水是一般和個別的關(guān)系。另外,中國傳統(tǒng)詮釋學(xué)的思想元素也十分的深邃和豐富,例如,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注郭象;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疏不駁注,注不駁經(jīng);六經(jīng)責(zé)我開生面;注者比作者更善巧。藏族諺語;照著講與接著講。馮友蘭;師造化、師古人;筆墨當(dāng)隨時代。經(jīng)世致用;心外無物。中國文人畫,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其思想基礎(chǔ)也是詮釋學(xué),例如國畫大師齊白石說: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
二、歷史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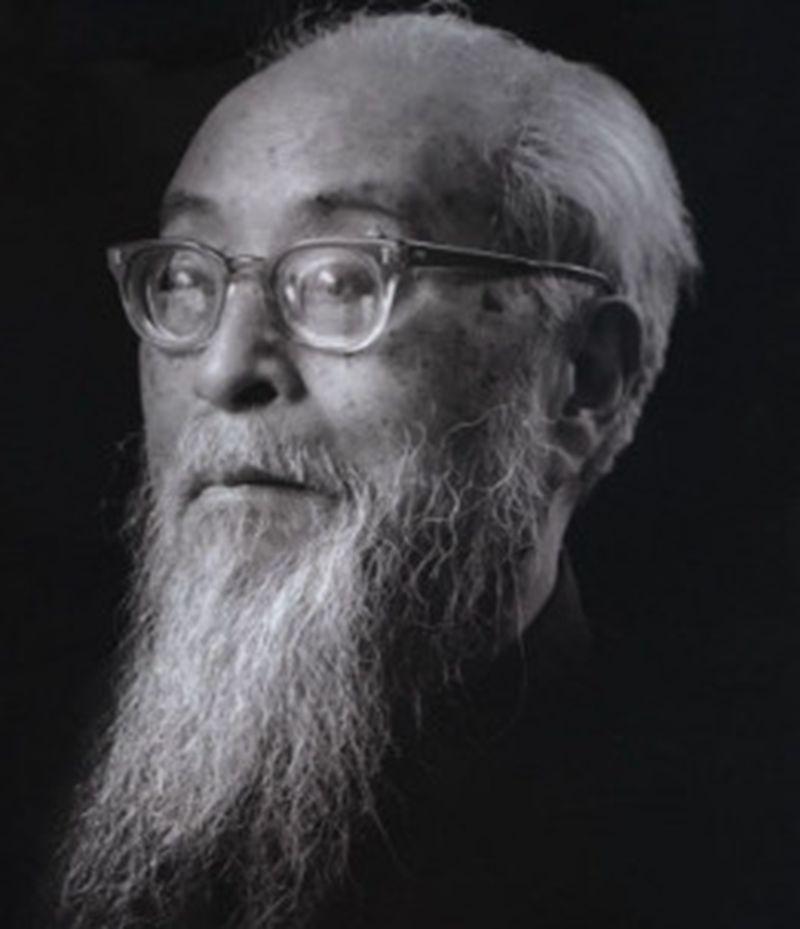
中國哲學(xué)家馮友蘭
關(guān)于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馮友蘭先生分為三個階段,“中國佛教和佛學(xué)的發(fā)展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稱為格義,第二個階段稱為教門,第三個階段稱為宗門。”這里馮先生所謂“格義” 階段 ,就是佛教中國化的初期階段。海德格爾與伽達(dá)默爾哲學(xué)詮釋學(xué)提出的前理解、前見解這一詮釋學(xué)理念,似可說與中國佛教史上的“格義”相類似,它為中國佛教的本土化過程和體系重構(gòu)提供基礎(chǔ)性詮釋和論證。例如據(jù)《高僧傳》說:
(竺)法雅,河間人。……少善外學(xué),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咨稟。時依雅門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jīng)中事數(shù),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xùn)門徒。
格義的關(guān)鍵是“以經(jīng)中事數(shù),擬配外書”,即以中土本有的經(jīng)典(“外書”)對應(yīng)佛教“事數(shù)”(如五蘊(yùn)、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等),所謂量度經(jīng)文,正明義理即格義也。也就是用中國固有哲學(xué)的概念、詞匯和觀念來比附、連類和解釋印度佛教的經(jīng)典及其思想,由此形成了“格義”式的佛教哲學(xué),它是佛教,而在思想上又是中國的。漢地佛教之東漢、三國、西晉時代的佛教哲學(xué)都帶有明顯的“格義”色彩。
無論對解釋者和解釋者的聽眾來說,“格義”都是以大家已經(jīng)熟知的經(jīng)典和概念來解釋大家尚未熟悉的思想理論概念。簡單地說,傳統(tǒng)的“格義”是以固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經(jīng)典中的概念解釋尚未普及的、外來文化的基本概念的一種臨時的權(quán)宜之計(jì)。這種人們與生俱來、積習(xí)既久的前意識在其思想形成過程中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在談到北宋理學(xué)家張載時曰:
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jīng)。……與二程道學(xué)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xué),淳如也。……載古學(xué)力行,為關(guān)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
在論及宋明理學(xué)家程顥時亦曰:
……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xué),遂厭科舉之習(xí),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jīng)而后得之。
由上所引觀之,張載與程顥深受傳統(tǒng)儒學(xué)思想之熏染,由此而形成的結(jié)構(gòu)性前見、前有、前把握,便決定他們必然要走“‘由儒而釋,由釋返儒,客隨主便’的心路歷程。”佛教在西藏傳播的初期,也采用了“格義”式的詮釋途徑。松贊干布“針對蕃人的狀況,用諸苯波、第吳、仲居的模式引導(dǎo)蕃地屬民信奉佛法。”《柱間史》又說道:“為領(lǐng)悟佛之教言,故而開示‘仲’;為通達(dá)佛之義理,故而開示‘第吳’;為知曉佛之三學(xué),故而開示‘雍仲苯’。”《賢者喜宴》說:“在藏地未來密咒和律藏出現(xiàn)的前兆是出現(xiàn)‘天神苯先波切’及苯教義理;經(jīng)藏出現(xiàn)的前兆是興起了‘仲’;論藏出現(xiàn)的前兆是介紹了‘第吳’。”這些便是藏民族接受佛教的思想前見和前意識。
綜上所講,在理解和詮釋印度佛教經(jīng)典原義、作者原意時,中國的理解者和詮釋者之間形成了“視域融合”,“格義”本身就是兩者視域融合的集中體現(xiàn)。它所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shí)效益就是“效果歷史”。效果歷史概念揭示了詮釋學(xué)另一重要功能即應(yīng)用功能。按照浪漫主義詮釋學(xué)的看法,詮釋學(xué)只具有兩種功能,即理解功能和解釋功能,而無視它的應(yīng)用功能。伽達(dá)默爾根據(jù)古代詮釋學(xué)、特別是法學(xué)詮釋學(xué)和神學(xué)詮釋學(xué)的實(shí)踐,強(qiáng)調(diào)了應(yīng)用在詮釋學(xué)里的根本作用。他認(rèn)為,我們要對任何文本有正確的理解,就一定要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和某個具體的境況里對它進(jìn)行理解,理解在任何時候都包含一種旨在過去和現(xiàn)在進(jìn)行溝通的具體應(yīng)用。
這樣一個視域融合語境下呈現(xiàn)出來的具體應(yīng)用,即本土化、中國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它體現(xiàn)在制度儀軌,神靈譜系,思想義理,修持實(shí)踐,行為規(guī)范,文化要素等方面本土化、中國化的表現(xiàn)。佛教中國化,其中教義思想的本土化、中國化是十分深邃的哲學(xué)問題。以藏傳佛教佛教之般若中觀為例,宗喀巴大師說,龍樹、提婆以般若經(jīng)為依據(jù),創(chuàng)立中觀論(中道觀),此謂籍經(jīng)立論也。佛護(hù)、清辨、智藏、月稱、寂護(hù)依龍樹中觀論創(chuàng)造中道論之諸支系。前者稱為本源性中觀師,后者叫作有偏向性中觀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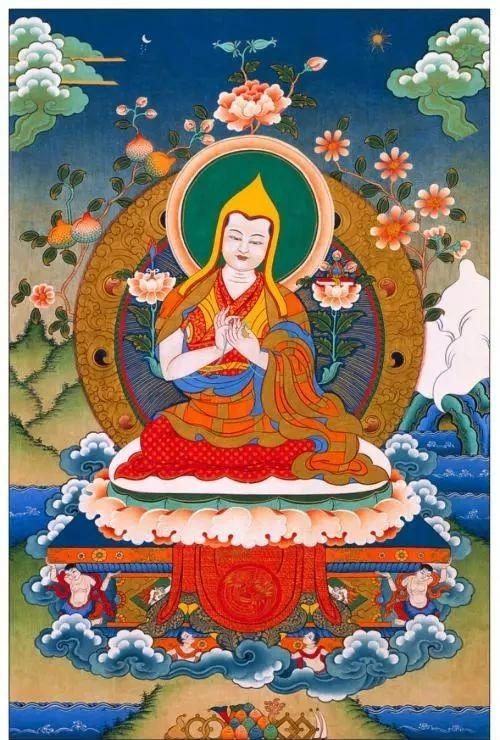
藏傳佛教格魯派創(chuàng)始人宗喀巴大師
又有藏地之一類昔賢或大善知識對此中觀師作如是言:“就從名言世俗境而立名者,略于二類大中觀師,謂于名言許外境者,名經(jīng)部行中觀師;及于名言不許外境者,名瑜伽行中觀師。謂許勝義諦現(xiàn)空雙聚,名理成如幻,及許勝義諦唯于現(xiàn)境絕斷戲論,名極無所住。”這便是典型的籍論立宗。這是說,藏人昔賢將印度佛教般若中觀師徒之文瀾往復(fù),思緒曲折的過程勾勒、整合、命名為世俗諦向度之經(jīng)部中觀與瑜伽中觀,勝義諦視角之現(xiàn)空雙聚與極無所住。這是宗喀巴對藏傳佛教般若中觀本土化進(jìn)程的歷史闡釋與標(biāo)志性定位。
宗喀巴將中觀應(yīng)成與自續(xù)兩大概念溯源至后弘期藏人智者,“雪山叢中后弘教時,有諸智者于中觀師安立二名,曰應(yīng)成師及自續(xù)師。此順《明句論》故非杜撰。故就名言許不許外境定為二類。”這是藏族佛教學(xué)者對印度佛教般若中觀義的集中分類,基本概括和準(zhǔn)確命名,是佛教義理本土化、中國化的典型個案。
又例如,在漢傳佛教中,東晉時期,當(dāng)時的佛教學(xué)者往往與玄學(xué)的觀點(diǎn)去理解和闡釋《般若經(jīng)》的思想,對《般若經(jīng)》所謂“空”的意義理解不一形成了“六家七宗”,這些般若學(xué)流派實(shí)際上是魏晉玄學(xué)不同流派的變相。般若學(xué)正是在與玄學(xué)的結(jié)合中得到廣泛傳播的。僧肇在充分理解把握般若學(xué)經(jīng)論原義的基礎(chǔ)上撰寫了《不真空論》等文,準(zhǔn)確地闡發(fā)了空宗的要義。批評了六家七宗對般若中觀不甚準(zhǔn)確的理解,僧肇的“非有非無”的“不真空”論,既是對佛教般若學(xué)六家七宗的批判總結(jié),也是對魏晉玄學(xué)的有無之辯的批判總結(jié)。這樣就形成了般若中觀之文本原義,作者原意之普遍性、統(tǒng)一性與不同時空境遇下的人們對其理解與詮釋學(xué)的個體性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
據(jù)此筆者提出:佛教義理的本土化、中國化它既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要素上的改觀,又反映在內(nèi)涵性質(zhì)上的深化;它既有量變,又有部分質(zhì)變;既有同質(zhì)與異質(zhì)的內(nèi)外融攝,又有同質(zhì)性的內(nèi)部各要素間的會通,這是“佛以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的佛教覺解本體論,亦是共殊本體詮釋學(xué)。總之,中國佛教的教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攝融與通和,勿用諱言,它依賴于從古印度翻譯而來的思想存貨,但它是在中國的經(jīng)濟(jì)政治思想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滋養(yǎng),涵化而形成的,它的歷史過程一方面是殊相,生成,會通,創(chuàng)造。另一方面又是普遍,統(tǒng)一,共相。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具體的共相”。用通俗的話說:“熟悉的陌生人”。
三、現(xiàn)實(shí)維度
伽達(dá)默爾的詮釋學(xué)本身就是一門現(xiàn)實(shí)的實(shí)踐的學(xué)問。可謂是學(xué)以致用也。佛教講“隨順世間,隨轉(zhuǎn)眾生”。藏傳佛教講“覺悟等齊于佛,行為隨順于人”。佛教無國界,但每個佛教徒都有國籍、都屬特定的國家,國土在則佛法在,國土安則佛法興。這是“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道理。因此,佛教提出“莊嚴(yán)國土,利樂有情”的理念。以下兩段佛經(jīng)中的話語清楚闡述了此思想。
爾時,佛告五百長者:「善哉善哉!汝等聞于贊嘆大乘,心生退轉(zhuǎn)發(fā)起妙義,利益安樂未來世中,不知恩德一切眾生。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我今為汝分別演說世出世間有恩之處。善男子!汝等所言未可正理。何以故?世出世恩有其四種: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如是四恩,一切眾生平等荷負(fù)。國王恩者,······以是因緣,成就十德:一名能照,以智慧眼照世間故。二名莊嚴(yán),以大福智莊嚴(yán)國故。三名與樂,以大安樂與人民故。四名伏怨,一切怨敵自然伏故。五名離怖,能卻八難離恐怖故。六名任賢,集諸賢人評國事故。七名法本,萬姓安住依國王故。八名持世,以天王法持世間故。九名業(yè)主,善惡諸業(yè)屬國王故。十名人主,一切人民王為主故。一切國王以先世福,成就如是十種勝德。······以是因緣,違順果報(bào)皆如響應(yīng)。圣王恩德廣大如是。三寶恩者,名不思議利樂眾生無有休息,是諸佛身真善無漏,無數(shù)大劫修因所證,三有業(yè)果永盡無余,功德寶山巍巍無比;一切有情所不能知。福德甚深猶如大海,智慧無礙等于虛空,神通變化充滿世間,光明遍照十方三世;一切眾生煩惱業(yè)障,都不覺知。沈淪苦海生死無窮,三寶出世作大船師,能截愛流超升彼岸,諸有智者悉皆瞻仰。善男子等!唯一佛寶具三種身: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變化身。
大王!以王因緣,國土安樂,人民熾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樂此國,持戒精勤,修習(xí)正道。大王!我經(jīng)中說,若出家人隨所住國,持戒精進(jìn),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
以上經(jīng)典話語說明,愛國愛教,護(hù)國利民,如理如法,契理契機(jī)是佛教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基本義理所在,也是自古至今中國佛教傳承、弘揚(yáng)和踐行的基本理念和行為準(zhǔn)則。

四、余論
詮釋學(xué)是關(guān)于理解與解釋的學(xué)說,而全部理解與解釋,都是指向文本原義與解釋者之間互動而達(dá)成的視域融合,其結(jié)果既一又異。這就如繪畫中的原型與摹本,原型固然優(yōu)于摹本,但是原型只有通過摹本才能達(dá)到表現(xiàn)和繼續(xù)存在的功能。因此,原型是在表現(xiàn)中才能達(dá)到自我表現(xiàn),表現(xiàn)對于原型來說,不是附屬的事情,而是屬于原型自身的存在,原型正是通過表現(xiàn)才經(jīng)歷了一種在空間的擴(kuò)展與時間的持續(xù)性。這樣便顛覆了以往一種傳統(tǒng)觀念關(guān)于本質(zhì)和現(xiàn)象,實(shí)體與屬性,原型與摹本的主從關(guān)系,原來認(rèn)為是附屬的東西現(xiàn)在起了主導(dǎo)作用。
如果用此詮釋學(xué)觀照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便會發(fā)現(xiàn):印度佛教文本經(jīng)論律與中國人之理解、闡釋之間互動而達(dá)到了化境的結(jié)果。它既保持佛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義、基本功修,又堅(jiān)守中國立場,堅(jiān)持中國本位,在佛教設(shè)施、禮儀、神譜、體制、教義方面入鄉(xiāng)隨俗,因地制宜,努力尋求中國化的表達(dá)方式和表現(xiàn)方式;既謹(jǐn)守師法,強(qiáng)調(diào)師徒授受,又主動適應(yīng)中國社會,積極認(rèn)同主體文化,運(yùn)用會通創(chuàng)新、嫁接求異的中國人思維方式,促使佛教教義同中國文化相契相融;既注重佛教的傳承淵源與義理原旨,又在某些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和重要領(lǐng)域植入中國人的思想方法,展現(xiàn)中華文化氣象,不重復(fù)不相類印度佛教的面相。
深度揭示是中國佛教,而不是佛教在中國;是中國化佛教,而不是佛教化中國的歷史進(jìn)程與真實(shí)形態(tài),它體現(xiàn)了不易與變易、殊相與共相的覺解本體論。從此邏輯起點(diǎn)出發(fā),中國佛教的本土化便具有其必然性、合法性、合理性。這便是本文試圖在中國佛教發(fā)展史與中西佛詮釋學(xué)結(jié)合的基礎(chǔ)上提出的“共殊本體詮釋學(xué)”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