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才讓,詩人、當(dāng)代藏族作家,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甘肅省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達(dá)賽爾》雜志編委會(huì)委員,甘南州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青海省貴德縣仁人,在國內(nèi)報(bào)刊雜志上發(fā)表大量小說、詩歌、散文、評(píng)論等文藝作品。先后榮獲首屆全國“崗尖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獎(jiǎng)等16種獎(jiǎng)項(xiàng)。詩歌集《黎明天女的召喚》榮獲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h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銅奔馬”獎(jiǎng);2009年,中篇小說《夢(mèng)想與現(xiàn)實(shí)》榮獲甘肅省第五屆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獎(jiǎng)一等獎(ji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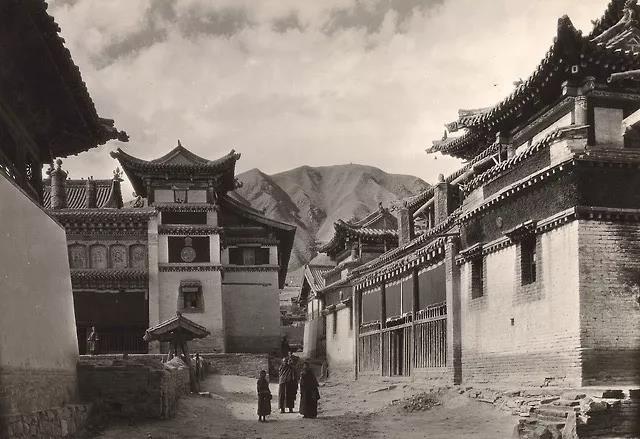
“你是從遠(yuǎn)古的草原上飄來的一只船,載馱著千年恒久的歷史,背伏著唱不完的歌,還有愛,將你巨大的身影投融我的視野。”當(dāng)?shù)仄骄€上涌來牛群,日月從牛角尖起升滑落時(shí),拉加才讓的詩情之弦被這瞬間一閃而過的風(fēng)景觸撥,完成了《牦牛》這首詩。當(dāng)然,還有許多詩、小說、散文,傾注著他對(duì)這片高原的真心,變成一排排、一行行鉛字,呈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只要領(lǐng)略過雪山沉默凝鑄的情懷,感受過樸實(shí)無華的坦誠,就能讀懂這一首首詩歌后面沉浮的歲月蒼桑,以及歲月深深烙印在作者思想軌跡上的朱印。這也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客觀與主觀、作者與讀者之間不可避免的交流因果。這種主觀與客觀遇合的方式既能銜接創(chuàng)作工程中的斷路,又能拓伸作者的思路,使“因”源于沉思擇行,使果趨于策鞭規(guī)正。整個(g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具有了一種“全方位躍動(dòng)”,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之間才能升騰起一種自覺的文學(xué)意識(shí)。藏族文學(xué)正確的走向應(yīng)該是這樣的——至少我認(rèn)為。
一、《銀戒指》意味著什么?
?20世紀(jì)80年代是藏族文學(xué)歷經(jīng)十年浩劫后的復(fù)蘇、繁榮們發(fā)展的重要時(shí)期。拉加才讓和一大批同齡的青年作者一起生時(shí)代星空的照耀下,開始了莊嚴(yán)的筆耕季節(jié)。民族文化春潮股的洋溢,激動(dòng)著酣夢(mèng)初醒的青春;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的文學(xué)刊物,為這一批從社會(huì)邁進(jìn)大學(xué)的驕子們構(gòu)置了閃現(xiàn)理想霓虹的天幕;年輕的活力需要進(jìn)行精神的釋放,而精神世界的花邊鑲在文學(xué)的錦繡上方能綻放異彩。于是,寫詩、寫小說成為校園的一股潮流,后浪推前浪,大有波濤洶涌之勢(shì)。年輕的學(xué)子們,在呼嘯而過的歷史與傳統(tǒng)中把握著先哲們留存的信息,在來不及躲避各種學(xué)派思潮的沖擊中春意萌動(dòng),強(qiáng)調(diào)自我。拉加才讓和他們一樣,新鮮的大學(xué)生活終于替代了往日的沉悶,理想的結(jié)局已將企盼之心填充得圓滿而豐實(shí)。然而,那逝去的歲月、往日的年輪留在心中的跡印,卻永遠(yuǎn)滿含著眷戀,將那往事不斷地閃現(xiàn)。這回憶也許是峰下的一個(gè)清晨,濕霧彌漫,碧草如洗,甩響的牧鞭下牛羊涌動(dòng),白色的炊煙飄向空曠的天際;這回憶也許是校園腳下踩著吱吱作響的雪,吸著白色的霧氣,一個(gè)寒冬里的晨讀。也許只有回憶才能填充隨時(shí)被騰空的心房。于是當(dāng)拉加才讓思想與情感的雙翼增添了回憶與幻想的羽毛后,他便想凌空,迫不及待地講述《你的來信》,講述《銀戒指》的故事,截取一幅生活的畫面,表現(xiàn)他的取舍、審美。當(dāng)然,這種方式的使用在當(dāng)時(shí)曾很普遍。
《你的來信》獲《章恰爾》1981-1983年小說創(chuàng)作三等獎(jiǎng)。這篇小說描寫了兩個(gè)青年在相識(shí)相戀后相別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我們當(dāng)時(shí)最常見的那種熱忱、好學(xué)、念念不忘理想追求、時(shí)時(shí)勤奮上進(jìn)的青年。在一個(gè)偶然的時(shí)機(jī),他救了一個(gè)昏倒在地的姑娘。他們?cè)臼峭荒昙?jí)的校友,當(dāng)友誼的心繩將他們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時(shí)候,愛情也隨之萌生,單純幼稚的心靈總是被理想包圍著。當(dāng)他們告別校園走向社會(huì)的門檻時(shí),共同約定,在某個(gè)大學(xué)的校園里聚首。山盟海誓之后,男女主人公在各自不同的環(huán)境里沉浮錘煉。故事的結(jié)局最終在一個(gè)相聚的日子里宣告結(jié)束,不為別的,只為時(shí)過境遷,女主人公隨遇而安、隨波逐流的生存價(jià)值觀與男主人公不渝不悔的理想追求格格不人,他們只好各奔東西。這個(gè)典型的愛情故事正是80年代初期校園文學(xué)所表現(xiàn)的一個(gè)比較普遍的題材,也是作者這代人所經(jīng)歷過的生活的一段回憶。他們與作品中的主人公有著思想上的許多巧合,經(jīng)歷中的某些相似和回憶中的情感相吻合。我不敢說這個(gè)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是,這種愛情的經(jīng)歷曾經(jīng)是作者所熟知的許多人感情過程中的一種重疊。這種愛情大多有過男女主人公對(duì)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維系這種情感的紐帶往往是單純的理想,所以又是很脆弱的,經(jīng)不起時(shí)間與環(huán)境的考驗(yàn)。作為人類情感的愛情,永遠(yuǎn)是說不清道不白。它牽涉了人本身太多復(fù)雜的生理及心理因素,任何對(duì)這種感情的解釋,大多是徒勞的。所以先人們就妙用“緣”字概而括之,倒也叫人百思其義,永遠(yuǎn)猜不透也永遠(yuǎn)不會(huì)厭煩。《你的來信》以信開頭,以回憶為整個(gè)線索,勾描了一個(gè)愛情的故事。但是給人的感覺仍是一種漂浮在情節(jié)水面上的浮萍,一種負(fù)載語言符碼的殼體組織。作品內(nèi)在的積淀在符碼底下的心理流程中則很少涉及。然而,作者在他的另一篇小說《銀戒指》中,對(duì)人物形象的塑造,從心理描寫、語言對(duì)白和情景的渲染方面進(jìn)行了在當(dāng)時(shí)說來算比較成功的探索。對(duì)于一個(gè)喜新厭舊、婚戀情變的古老話題來講,《銀戒指》仍然是這種舊話的重提。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那些充滿溫馨的童年回憶曾在仁措心中激蕩過純真而美麗的漣漪,一聲聲親切的“阿佳桑珠”、“仁措妹妹”,一起扮演過“家里”的小大人模樣,一塊兒在河邊田地嬉笑連天的昨日都凝結(jié)在桑珠的愛情定物——銀白色的戒指上,成為仁措無怨無悔的記憶,珍藏在內(nèi)心深處。當(dāng)這位美麗、善良,對(duì)生活充滿真切的愛和留戀、毫無奢望和怨言的少女遭受桑珠的遺棄,感情的厄運(yùn)向她襲來時(shí),她仍然沉默著不為自己應(yīng)有的權(quán)力去爭取。她的純與真不能為自己換取一個(gè)抵御和防護(hù)的外套。就這樣一個(gè)少女最美好的情感記憶,竟布滿了層層痂痕,最后隨著那丟棄了的銀戒指一同流滲到了內(nèi)心的深處。帶著這層傷痛,她的手指也許會(huì)在不久的將來再戴一枚同樣的銀戒,然而刻在生命之旅的記憶將陪伴她整個(gè)一生。無論是否飽享幸福,都不會(huì)忘卻。仁措的形象,很容易將我們的思緒牽引到一個(gè)很敏感的話題,這就是在當(dāng)今這個(gè)時(shí)代,藏族婦女特別是農(nóng)村婦女對(duì)自身的權(quán)利、價(jià)值、尊嚴(yán)是否覺悟。盡管作者講述完這個(gè)故事,并未提出任何圍繞著這層意蘊(yùn)鋪展開的情節(jié)與對(duì)話,但是那無形的、導(dǎo)致這場(chǎng)愛情悲劇的真正原因,還是要向極為復(fù)雜、根深蒂固的、游蕩在我們周圍那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及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尋找答案。
桑珠,這個(gè)曾經(jīng)充當(dāng)過仁措心中完美的“阿佳”的人在平和出眾的面容下隱藏著一顆充滿了陰暗私欲的心,當(dāng)攀附的階梯沿伸而來時(shí),他急不可待地用鄉(xiāng)村學(xué)校中所得的一點(diǎn)知識(shí)充當(dāng)行囊,將山盟海誓的表演托掛在一枚銀戒上,匆匆忙忙奔向他渴望許久、可以抖落滿身泥巴的另外一種環(huán)境,在另個(gè)課堂中去找尋提高個(gè)人身價(jià)的鑰匙。這種人,私利一旦得呈,丟掉了農(nóng)家子弟的敦厚與純樸,用出賣自己良知的契約換回一張城市戶口,一頂烏紗帽。三年后的一天,他又重返故土,儼然一副干部模佯,再傍系一位異族女人,鄉(xiāng)音已改,滿口酸氣。我們?cè)诒梢曔@個(gè)勢(shì)利小人時(shí),又對(duì)他在“女士”面前流露的那種卑膝屈下、誠惶誠恐感到可憐。他的后半生或許會(huì)在良知的醒悟中掙扎,或許會(huì)在掙扎中麻木不仁,總之,那銀色的戒指不會(huì)像沖進(jìn)河里的泥沙溶入水中,而會(huì)在記憶的深處閃爍出令人心顫的往事。
小說隨著銀戒的丟棄而完結(jié)了。作者只是平靜地講述了這個(gè)故事。然而,環(huán)繞在故事中的氣氛,使我們深思良久,也許拉加才讓對(duì)他筆下的女性都抱有正義的同情,塑造她們的同時(shí)念念不忘傳統(tǒng)女性善良而柔弱、樸素而混沌的形象。但是,我們依舊會(huì)從仁措身上烙印著的深刻而廣泛的社會(huì)內(nèi)容和歷史性中讀出作品的畫外音。也許,這也是作者想表現(xiàn)的深層內(nèi)涵。
20世紀(jì)80年代的藏族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在深刻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注重人物形象塑造、努力用大眾化的口語去表達(dá)作者愛憎的同時(shí),除極少數(shù)作者不斷廣拓思路、從自己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養(yǎng)份、兼顧整個(gè)文學(xué)的發(fā)展趨向以外,大多數(shù)作品仍在講述著古老的故事,追求著完整的情節(jié),渴望自己的作品能給人以教育和啟示,刻意表現(xiàn)鮮明的意圖,并且在作者對(duì)自身的個(gè)性投射上還顯現(xiàn)著迷蒙狀態(tài)。所以,重大的歷史體裁、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和個(gè)性鮮明的具有真正高原氣質(zhì)的人物形象還很缺乏。這需要我們的作家冷靜思考,需要自身的調(diào)養(yǎng),需要自我的提高。
《銀戒指》的作者是個(gè)悟性很強(qiáng)的人。“悟”的過程就是不斷剖析自己、重估自己的過程。這中間他必須知道自己的個(gè)性,懂得自己的胃適合容納什么樣的飯菜。只有懂得取舍、了解自己氣質(zhì)的作家才能形成他不同于別人的風(fēng)格。單一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并不代表作者能力的大小,博采的目的是為了解、豐潤自己,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獨(dú)立性,而不是在“博”中湮沒自己。

二、花之心戀
?藏民族是一個(gè)善于用詩歌表現(xiàn)自身精神世界弘大廣博、物相世間滄桑曠遠(yuǎn)的民族。年輕的詩人都曾在這片眩目的詩之灼光下敞開心胸盡情吸納、瞻仰祖輩遺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真誠歌唱雪域母親,贊美江河之源的廣袤。這些都是新生代年輕詩人們共同的心聲。拉加才讓的《牦牛》就是這樣一群涌動(dòng)而來的地平線上的牛群。在人跡罕至的雪線上,牦牛頑強(qiáng)的生命力不正昭示著這個(gè)民族剛毅、堅(jiān)定、不屈不撓的精神嗎?“當(dāng)日月從你的角間升落/綠草在你的蹄印里枯榮/你的目光深處/分明流露著情感/觀望正吮吸著你乳汁的孩子……”這個(gè)被詩人人格化了的牦牛多像一位沉穩(wěn)的母親,當(dāng)紫色的草穗隨風(fēng)搖曳,當(dāng)溫?zé)岬呐<S火烘干每一件潮濕的衣衫,當(dāng)人們手捧濃香的奶茶,沉默的牦牛啊,你已經(jīng)走過了太長的路,馱載了太多的經(jīng)歷,牧人的喜怒哀樂都會(huì)在你的風(fēng)景線里筑巢,夏季的牧場(chǎng)正等待著你和你的主人們。牦牛,用它的忠誠與沉靜感動(dòng)了詩人。在這里,作為“高原之舟”的牦牛不再單單以它的本性去點(diǎn)綴詩句,而是透過一字一句,使我們感悟到一種特有的民族精神氣質(zhì):剛強(qiáng)而不失柔韌。真實(shí)來源于腳踏實(shí)地的行進(jìn),這是《牦牛》的啟示。
作為詩人,拉加才讓在表現(xiàn)他主觀世界形形色色的感受悟過程時(shí),竭力擺脫那些表相的描寫,從身邊的每一件事、每一個(gè)感動(dòng)心靈的畫面去發(fā)現(xiàn)隱蔽的意象化的主題。他寫自然界的風(fēng)雨雷電,并不是將自然的壯觀美景用語言符碼定格在視線里,成為思維過程中的點(diǎn)綴美景,而是通過它們?nèi)グl(fā)掘歷史與人生的某一個(gè)吻合點(diǎn),承載思想之舟的港口,并沿著這個(gè)時(shí)空隧道去觸摸往昔的歲月,傳達(dá)一種時(shí)代的精神和自己的審美個(gè)性。《石·火·風(fēng)》就是蘊(yùn)含著這種基調(diào)的詩。“土地生就了我/可水鑄造了我/我無笑容可贈(zèng)/是因?yàn)橐研ν?我無腳可走/是因?yàn)橐炎咄?我無溫暖/是因血已流盡”,這塊普普通通的大石躺在曠野中,沐浴時(shí)光的晨露暮雨,所有的活力都曾隨著滄桑的變遷而消失殆盡,但是,這塊巨石是精神恒久不死的象征,腥風(fēng)血雨的古戰(zhàn)場(chǎng)、風(fēng)和日麗的夏季牧場(chǎng)、獵獵翻飛的經(jīng)幡桑煙都曾在它身邊留駐。這是歲月恒古如斯的長壽兒,目睹過羅剎女和彌猴相親相愛,聶尺贊布沿天繩而降和廢墟前期雍布拉崗的宏闊。“我是遠(yuǎn)古歷史的證人/更是未來建設(shè)者手中的基石”。
?詩在最后一句點(diǎn)明了自己—是一塊奠基未來的基石。歷史與未來在這塊基石上得以聚合。那么,詩的機(jī)緣就是拉加才讓通過基石來表現(xiàn)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的新生代看似冷漠、實(shí)則滾燙的心扉,展示這個(gè)民族傳承下來的高闊寬容的心態(tài)和對(duì)美好未來的追求精神。在詩歌的領(lǐng)域中,拉加才讓正如他在《風(fēng)》中所寫的那樣,“我是無形無影的流浪兒/擁有無限的自由去張飛”。心靈的自由感本源于精神世界的富足。當(dāng)他渴望如輕風(fēng)一般將自己的能量輸送給帳篷,為辛勞一生的牧人攜去雪蓮的清香;撲進(jìn)學(xué)校的窗口,在小姑娘甩動(dòng)的發(fā)辮上,為她送去祝愿與問候時(sh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對(duì)自身及社會(huì)投注的熱情以詩的方式展現(xiàn),使我們可以更廣闊地聯(lián)想到作者的總體意圖,即那種對(duì)本土生活的眷戀,并由此而抒發(fā)的一切真情實(shí)感。一個(gè)作者最主要的莫過于尋找到站立自身的根基。也只有在雪山環(huán)繞、青草鋪地的這片高原上,詩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時(shí)時(shí)觸動(dòng)心扉的感覺。拉加才讓熟悉故土的山山水水,熟悉那純樸親切的鄉(xiāng)音,那還未被鋼筋水泥澆注過的空間清純、怡人、原始質(zhì)樸的自然之美。天籟之聲不需要人工刻意去制造就可撲面而來。這種本土文化熏陶著詩人正如歌手總要歌唱母親一樣,拉加才讓也要將一往深情投注在對(duì)故土對(duì)民族的摯愛之上。這也是新生代藏族年輕詩人的一個(gè)共同點(diǎn)。他們對(duì)自己民族的描寫沒有語言上的障礙和生活的隔膜,像酥油融化于茶一般地與這里的一切渾然天成,無需去獵取一些奇風(fēng)異俗招搖過市,更無需為所謂外顯的民族特色而絞盡腦汁。他們身上本來就流注著這個(gè)民族文化習(xí)俗的深層次暗流,可以說創(chuàng)作的機(jī)緣都源于他們自然而然地觀察到的這種生活,源于他們對(duì)這片高原的摯愛與真誠。盡管他筆下反映的人生、揭示的人性和精神世界形形色色,但都充滿著民族的生活色彩和現(xiàn)實(shí)。這是拉加才讓和他的同行們共同擁有的。 ? ?

拉加才讓的創(chuàng)作生涯已有十幾個(gè)年頭。在這段時(shí)間,他竭力摒棄那種主題鮮明、情節(jié)化、故事化的初期創(chuàng)作模式,自覺地追求著寓意的深廣和人性的多層性、復(fù)雜性及廣闊性的創(chuàng)作方式。尤其是在詩歌的創(chuàng)作中更能感受到他追求的那種象征意義下蘊(yùn)含的情感力度。這種藝術(shù)把握方式,除了不斷豐富作者自身的知識(shí)閱歷和加深思想深度外,還能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思索空間和寓意的寄托。這無疑是一種好的趨勢(shì),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那是獨(dú)一無二的,別人無法替代的創(chuàng)作氣質(zhì)。創(chuàng)作個(gè)性的形成要經(jīng)過作者長時(shí)間的諦視和觀察客觀世界,尋找一種審美的方式,領(lǐng)略生活中的真善美與假惡丑并要超越自我。一個(gè)作家真正的投入創(chuàng)作,實(shí)際上是一種自我的創(chuàng)造。你的作品替你訴說了一切。所以,既然你已選擇了創(chuàng)作之路,既然你義無反顧地向妙音仙女叩拜,那么,你就要有種“早于他人構(gòu)建自由心境,奔向?qū)徝朗饺松钡臏?zhǔn)備,并為此要忍受寂寞、平淡,甚至放棄更多的世俗幸福。這是前提。離開了這一前提,你的作品只能是隨波逐流,成為藝術(shù)復(fù)制品的再版而已。
當(dāng)然,拉加才讓的職責(zé)是在三尺講臺(tái)上培育新人,創(chuàng)作仍是他的“業(yè)余職業(yè)”。在藏族傳統(tǒng)文化的祭壇上,他比別人更有機(jī)會(huì)接受精神的洗禮。這種洗禮理應(yīng)包括對(duì)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最富于傳承性的宗教知識(shí)載體的掌握,把握一個(gè)民族在宗教的精神殿堂里怎樣延續(xù)充滿人間煙火的世俗生活,探索文學(xué)怎樣從對(duì)神的附屬轉(zhuǎn)向?qū)θ说臍w皈。一句話,就是希望拉加才讓以他擁有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載負(fù)起更多的探索精神。讓我們以海明威的一段話作為該篇的結(jié)束語“對(duì)于一個(gè)真正的作家來說,每本書都應(yīng)該成為他繼續(xù)探索那些尚未到達(dá)的領(lǐng)域的一個(gè)新起點(diǎn)。他應(yīng)該永遠(yuǎn)嘗試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他人沒有做成的事。這樣他就有幸會(huì)獲得成功。?
